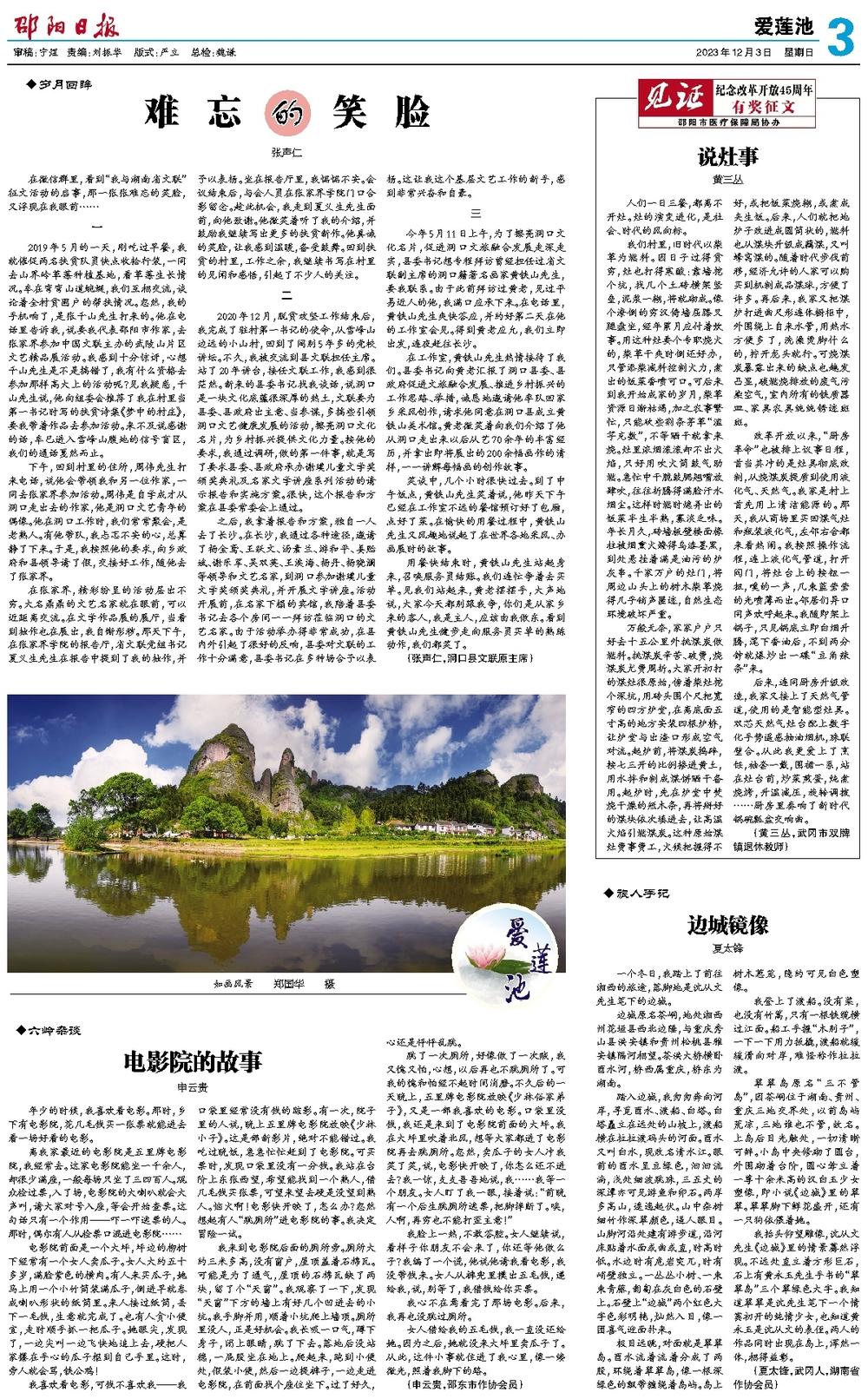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灶。灶的演变进化,是社会、时代的风向标。
我们村里,旧时代以柴草为燃料。因日子过得贫穷,灶也打得寒酸:靠墙挖个坑,找几个土砖横架竖垒,泥浆一糊,将就砌成。像个潦倒的穷汉倚墙屈膝叉腿盘坐,经年累月应付着炊事。用这种灶要个专职烧火的,柴草干爽时倒还好办,只管添柴减料控制火力,煮出的饭菜香喷可口。可后来到我开始成家的岁月,柴草资源日渐枯竭,加之农事繁忙,只能砍些荆条茅草“滥竽充数”,不等晒干就拿来烧。灶里浓烟滚滚却不出火焰,只好用吹火筒鼓气助燃。急忙中干脆鼓腮翘嘴放肆吹,往往折腾得满脸汗水烟尘。这样时燃时熄弄出的饭菜半生半熟,寡淡乏味。年长月久,砖墙板壁楼面椽柱被烟熏火燎得乌漆墨黑,到处悬挂着满是油污的炉灰串。千家万户的灶门,将周边山头上的树木柴草烧得几乎销声匿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万般无奈,家家户户只好去十五公里外挑煤炭做燃料。挑煤炭辛苦、破费,烧煤炭尤费周折。大家开初打的煤灶很原始,傍着柴灶挖个深坑,用砖头围个尺把宽窄的四方炉堂,在离底面五寸高的地方安装四根炉桥,让炉堂与出渣口形成空气对流。起炉前,将煤炭捣碎,按七三开的比例掺进黄土,用水拌和制成煤饼晒干备用。起炉时,先在炉堂中焚烧干燥的短木条,再将掰好的煤块依次填进去,让高温火焰引燃煤炭。这种原始煤灶费事费工,火候把握得不好,或把饭菜烧糊,或煮成夹生饭。后来,人们就把地炉子改进成圆筒状的,燃料也从煤块升级成藕煤,又叫蜂窝煤的。随着时代步伐前移,经济允许的人家可以购买到机制成品煤球,方便了许多。再后来,我家又把煤炉打进曲尺形连体橱柜中,外围绕上自来水管,用热水方便多了,洗澡烫脚什么的,拧开龙头就行。可烧煤炭暴露出来的缺点也越发凸显,碳燃烧排放的废气污染空气,室内所有的铁质器皿、家具农具统统锈迹斑斑。
改革开放以来,“厨房革命”也被排上议事日程,首当其冲的是灶具彻底改制,从烧煤炭提质到使用液化气、天然气。我家是村上首先用上清洁能源的。那天,我从商场里买回煤气灶和瓶装液化气,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我按照操作流程,连上液化气管道,打开阀门,将灶台上的按钮一扭,噗的一声,几束蓝莹莹的光喷薄而出。邻居们异口同声欢呼起来。我随即架上锅子,只见锅底立即白烟升腾,滗下香油后,不到两分钟就爆炒出一碟“豆角辣条”来。
后来,连同厨房升级改造,我家又接上了天然气管道,使用的是智能型灶具。双芯天然气灶台配上数字化手势遥感抽油烟机,珠联璧合。从此我更爱上了烹饪,袖套一戴,围裙一系,站在灶台前,炒菜煎蛋,炖煮烧烤,升温减压,旋转调拨……厨房里奏响了新时代锅碗瓢盆交响曲。
(黄三丛,武冈市双牌镇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