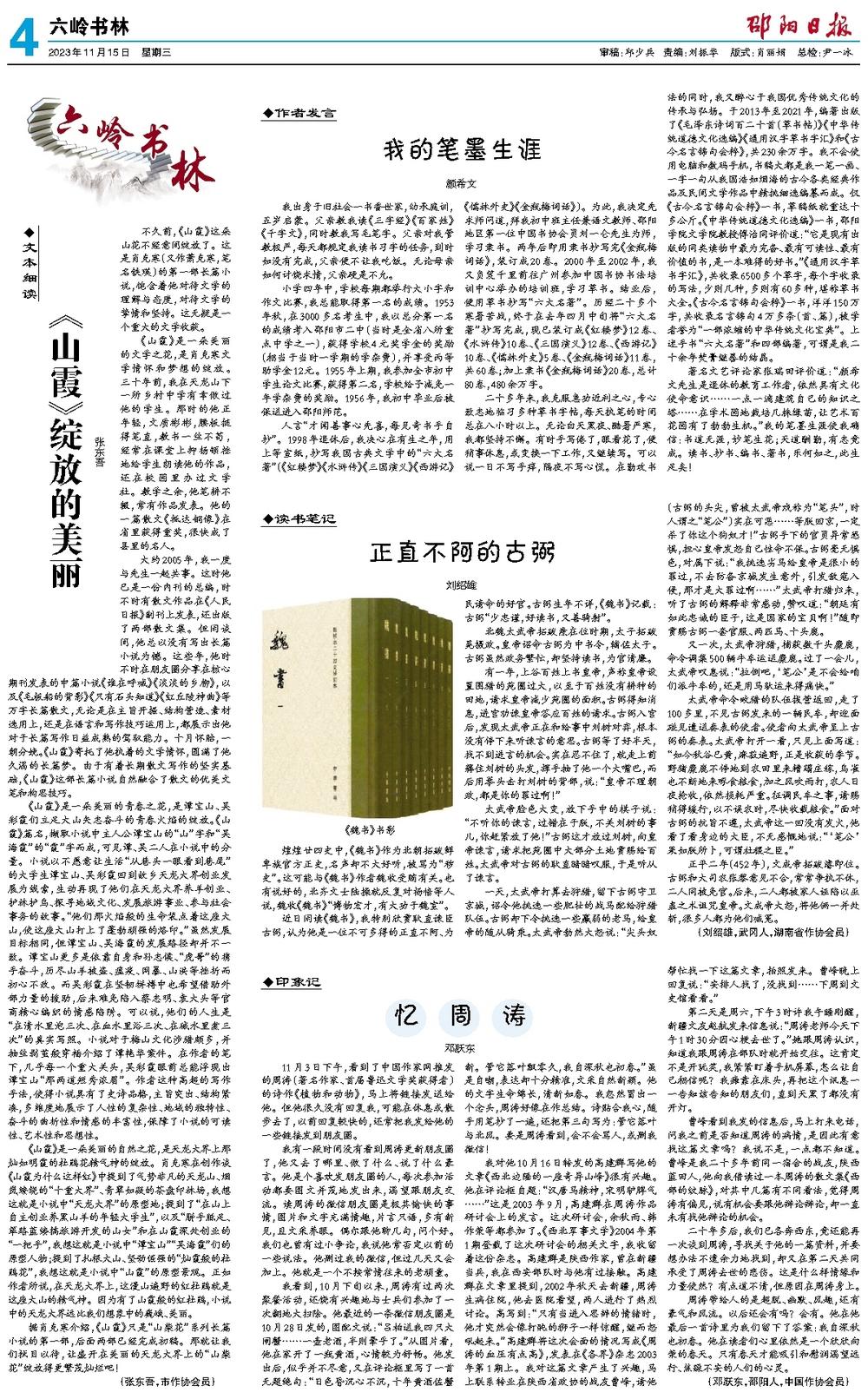不久前,《山霞》这朵山花不经意间绽放了。这是肖克寒(又作萧克寒,笔名铁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饱含着他对待文学的理解与态度,对待文学的挚情和坚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学收获。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文学之花,是肖克寒文学情怀和梦想的绽放。三十年前,我在天龙山下一所乡村中学有幸做过他的学生。那时的他正年轻,文质彬彬,腰板挺得笔直,教书一丝不苟,经常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给学生朗读他的作品,还在校园里办过文学社。教学之余,他笔耕不辍,常有作品发表。他的一篇散文《抵达铜像》在省里获得重奖,很快成了县里的名人。
大约2005年,我一度与先生一起共事。这时他已是一份内刊的总编,时不时有散文作品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还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但闲谈间,他总以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为憾。这些年,他时不时在朋友圈分享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中篇小说《谁在呼喊》《淡淡的乡柳》,以及《毛板船的背影》《只有石头知道》《红丘陵神曲》等万字长篇散文,无论是在主旨开掘、结构营造、素材选用上,还是在语言和写作技巧运用上,都展示出他对于长篇写作日益成熟的驾驭能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山霞》寄托了他执着的文学情怀,圆满了他久渴的长篇梦。由于有着长期散文写作的坚实基础,《山霞》这部长篇小说自然融合了散文的优美文笔和构思技巧。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青春之花,是谭宝山、吴彩霞们立足大山矢志奋斗的青春火焰的绽放。《山霞》篇名,撷取小说中主人公谭宝山的“山”字和“吴海霞”的“霞”字而成,可见谭、吴二人在小说中的分量。小说以不愿意让生活“从巷头一眼看到巷尾”的大学生谭宝山、吴彩霞回到故乡天龙大界创业发展为线索,生动再现了他们在天龙大界养羊创业、护林护鸟、探寻地域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参与社会事务的故事。“他们那火焰般的生命装点着这座大山,使这座大山打上了蓬勃顽强的烙印。”虽然发展目标相同,但谭宝山、吴海霞的发展路径却并不一致。谭宝山更多是依靠自身和孙志侯、“虎哥”的携手奋斗,历尽山羊被盗、瘟疫、网暴、山洪等挫折而初心不改。而吴彩霞在坚韧拼搏中也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的援助,后来难免陷入蔡志明、袁大头等官商精心编织的情感陷阱。可以说,他们的人生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真实写照。小说对于梅山文化涉猎颇多,并抽丝剥茧般穿插介绍了谭艳华案件。在作者的笔下,几乎每一个重大关头,吴彩霞眼前总能浮现出谭宝山“那两道短秀浓眉”。作者这种高超的写作手法,使得小说具有了史诗品格,主旨突出、结构紧凑,多维度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地域的独特性、奋斗的曲折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保障了小说的可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
《山霞》是一朵美丽的自然之花,是天龙大界上那灿如明霞的杜鹃花精气神的绽放。肖克寒在创作谈《山霞为什么这样红》中提到了气势非凡的天龙山、烟岚缭绕的“十重大界”、青翠如凝的茶盘印林场,我想这就是小说中“天龙大界”的原型地;提到了“在山上自主创业养黑山羊的年轻大学生”,以及“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搞旅游开发的山女”和在山霞深处创业的“一把手”,我想这就是小说中“谭宝山”“吴海霞”们的原型人物;提到了扎根大山、坚劲倔强的“灿霞般的杜鹃花”,我想这就是小说中“山霞”的原型景观。正如作者所说,在天龙大界上,这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就是这座大山的精气神。因为有了山霞般的红杜鹃,小说中的天龙大界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巍峨、美丽。
据肖克寒介绍,《山霞》只是“山柴花”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后面两部已经完成初稿。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让盛开在美丽的天龙大界上的“山柴花”绽放得更繁茂灿烂吧!
(张东吾,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