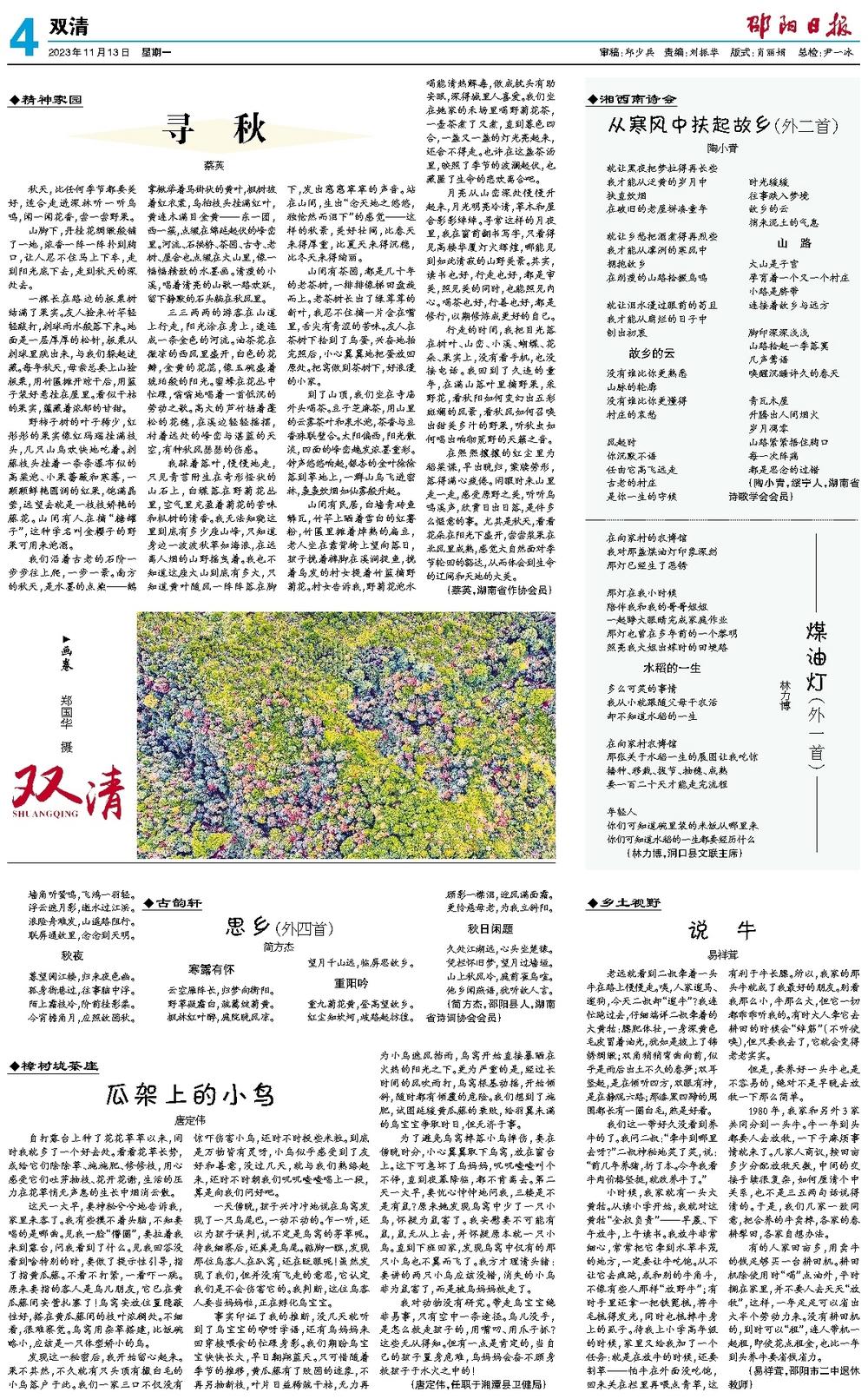老远就看到二叔牵着一头牛在路上慢慢走。咦,人家遛马、遛狗,今天二叔却“遛牛”?我连忙跑过去,仔细端详二叔牵着的大黄牯:膘肥体壮,一身深黄色毛皮冒着油光,犹如是披上了锦绣绸缎;双角稍稍弯曲向前,似乎是雨后出土不久的春笋;双耳竖起,是在倾听四方,双眼有神,是在静观六路;那漆黑四蹄的周围都长有一圈白毛,煞是好看。
我们这一带好久没看到养牛的了。我问二叔:“牵牛到哪里去呀?”二叔神秘地笑了笑,说:“前几年养猪,折了本。今年我看牛肉价格坚挺,就改养牛了。”
小时候,我家就有一头大黄牯。从读小学开始,我就对这黄牯“全权负责”——早晨、下午放牛,上午读书。我放牛非常细心,常常把它牵到水草丰茂的地方,一定要让牛吃饱。从不让它去疯跑,或和别的牛角斗,不像有些人那样“放野牛”;有时手里还拿一把铁篦梳,将牛毛梳得发光,同时也梳掉牛身上的虱子。待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家里又给我加了一个任务:就是在放牛的时候,还要割草——怕牛在外面没吃饱,回来关在栏里再喂点青草,这有利于牛长膘。所以,我家的那头牛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别看我那么小,牛那么大,但它一切都乖乖听我的。有时大人牵它去耕田的时候会“绊筋”(不听使唤),但只要我去了,它就会变得老老实实。
但是,要养好一头牛也是不容易的,绝对不是早晚去放牧一下那么简单。
1980年,我家和另外3家共同分到一头牛。牛一年到头都要人去放牧,一下子麻烦事情就来了。几家人商议,按田亩多少分配放牧天数,中间的交接手续很复杂,如何厘清个中关系,也不是三五两句话说得清的。于是,我们几家一致同意,把合养的牛卖掉,各家的春耕犁田,各家自想办法。
有的人家田亩多,用卖牛的钱足够买一台耕田机。耕田机除使用时“喝”点油外,平时搁在家里,并不要人去天天“放牧”,这样,一年足足可以省出大半个劳动力来。没有耕田机的,到时可以“租”,连人带机一起租,即使花点租金,也比一年到头养牛要省钱省力。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