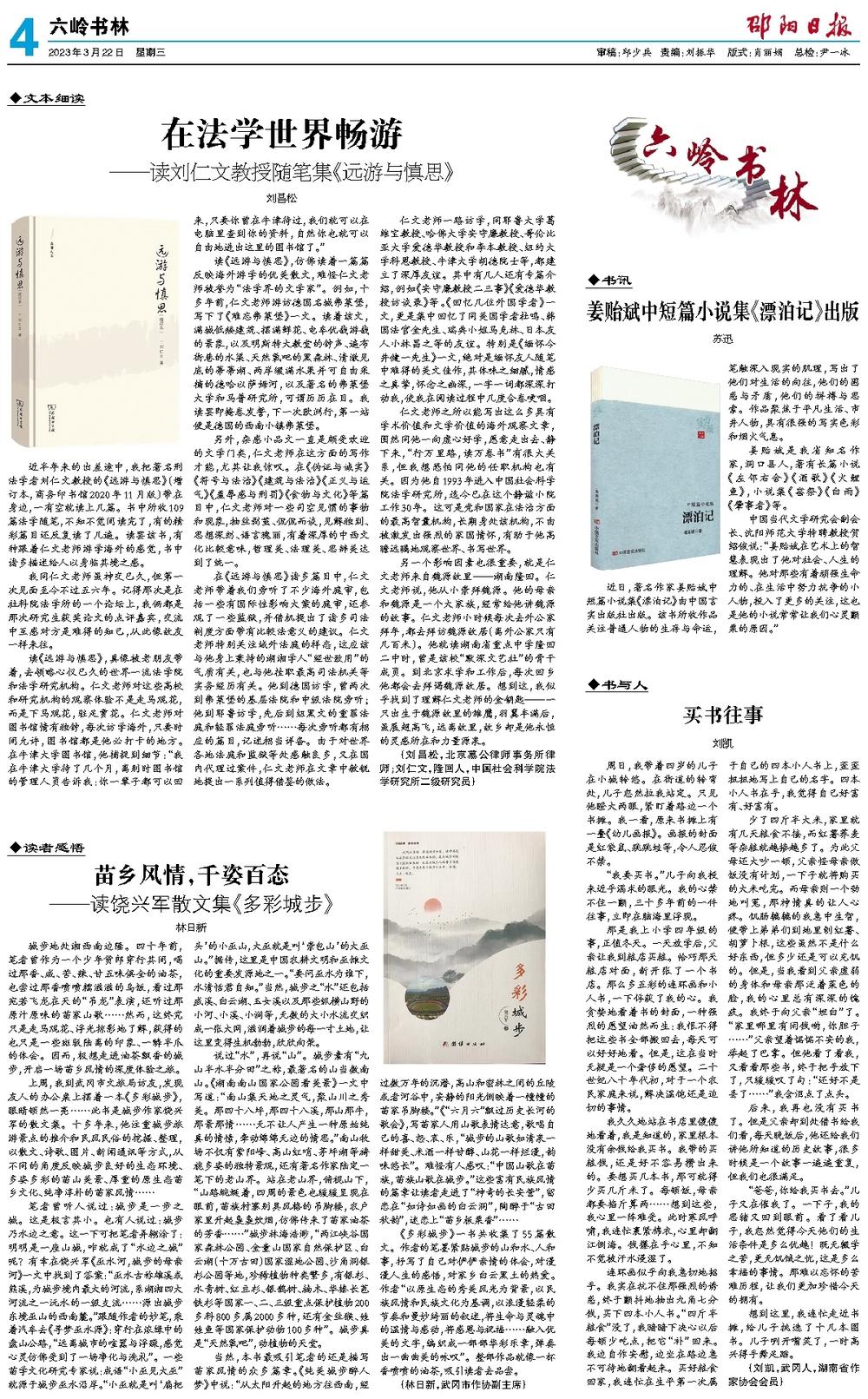近半年来的出差途中,我把著名刑法学者刘仁文教授的《远游与慎思》(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版)带在身边,一有空就读上几篇。书中所收109篇法学随笔,不知不觉间读完了,有的精彩篇目还反复读了几遍。读罢该书,有种跟着仁文老师游学海外的感觉,书中诸多描述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我同仁文老师虽神交已久,但第一次见面至今不过五六年。记得那次是在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个论坛上,我俩都是那次研究生获奖论文的点评嘉宾,交流中互感对方是难得的知己,从此像故友一样来往。
读《远游与慎思》,真像被老朋友带着,去领略心仪已久的世界一流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仁文老师对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观察体验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下马观花,驻足赏花。仁文老师对图书馆情有独钟,每次访学海外,只要时间允许,图书馆都是他必打卡的地方。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他捕捉到细节:“我在牛津大学待了几个月,离别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你一辈子都可以回来,只要你曾在牛津待过,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查到你的资料,自然你也就可以自由地进出这里的图书馆了。”
读《远游与慎思》,仿佛读着一篇篇反映海外游学的优美散文,难怪仁文老师被誉为“法学界的文学家”。例如,十多年前,仁文老师游访德国名城弗莱堡,写下了《难忘弗莱堡》一文。读着该文,满城低矮建筑、摆满鲜花、电车优哉游哉的景象,以及明斯特大教堂的钟声、遍布街巷的水渠、天然氧吧的黑森林、清澈见底的蒂蒂湖、两岸缀满水果并可自由采摘的德哈以萨姆河,以及著名的弗莱堡大学和马普研究所,可谓历历在目。我读罢即掩卷发誓,下一次欧洲行,第一站便是德国的西南小镇弗莱堡。
另外,杂感小品文一直是颇受欢迎的文学门类,仁文老师在这方面的写作才能,尤其让我惊叹。在《伪证与诚实》《符号与法治》《建筑与法治》《正义与运气》《羞辱感与刑罚》《食物与文化》等篇目中,仁文老师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和现象,抽丝剥茧、侃侃而谈,见解独到、思想深刻、语言瑰丽,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比较意味,哲理美、法理美、思辨美达到了统一。
在《远游与慎思》诸多篇目中,仁文老师带着我们旁听了不少海外庭审,包括一些有国际性影响大案的庭审,还参观了一些监狱,并借机提出了诸多司法制度方面带有比较法意义的建议。仁文老师特别关注域外法庭的样态,这应该与他身上秉持的湖湘学人“经世致用”的气质有关,也与他挂职最高司法机关等实务经历有关。他到德国访学,曾两次到弗莱堡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旁听;他到耶鲁访学,先后到纽黑文的重罪法庭和轻罪法庭旁听……每次旁听都有相应的篇目,记述相当详备。由于对世界各地法庭和监狱等处感触良多,又在国内代理过案件,仁文老师在文章中敏锐地提出一系列值得借鉴的做法。
仁文老师一路访学,同耶鲁大学葛维宝教授、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教授和李本教授、纽约大学科恩教授、牛津大学胡德院士等,都建立了深厚友谊。其中有几人还有专篇介绍,例如《安守廉教授二三事》《爱德华教授访谈录》等。《回忆几位外国学者》一文,更是集中回忆了同美国学者杜鸣、韩国法官金先生、瑞典小姐马克林、日本友人小林昌之等的友谊。特别是《缅怀今井健一先生》一文,绝对是缅怀友人随笔中难得的美文佳作,其体味之细腻,情感之真挚,怀念之幽深,一字一词都深深打动我,使我在阅读过程中几度合卷哽咽。
仁文老师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海外观察文章,固然同他一向虚心好学,愿意走出去、静下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有很大关系,但我想恐怕同他的任职机构也有关。因为他自199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迄今已在这个静谧小院工作30年。这可是党和国家在法治方面的最高智囊机构,长期身处该机构,不由被激发出强烈的家国情怀,有助于他高瞻远瞩地观察世界、书写世界。
另一个影响因素也很重要,就是仁文老师来自魏源故里——湖南隆回。仁文老师说,他从小崇拜魏源。他的母亲和魏源是一个大家族,经常给他讲魏源的故事。仁文老师小时候每次去外公家拜年,都去拜访魏源故居(离外公家只有几百米)。他就读湖南省重点中学隆回二中时,曾是该校“默深文艺社”的骨干成员。到北京求学和工作后,每次回乡他都会去拜谒魏源故居。想到这,我似乎找到了理解仁文老师的金钥匙——一只出生于魏源故里的雏鹰,羽翼丰满后,虽展翅高飞,远离故里,故乡却是他永恒的灵感所在和力量源泉。
(刘昌松,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