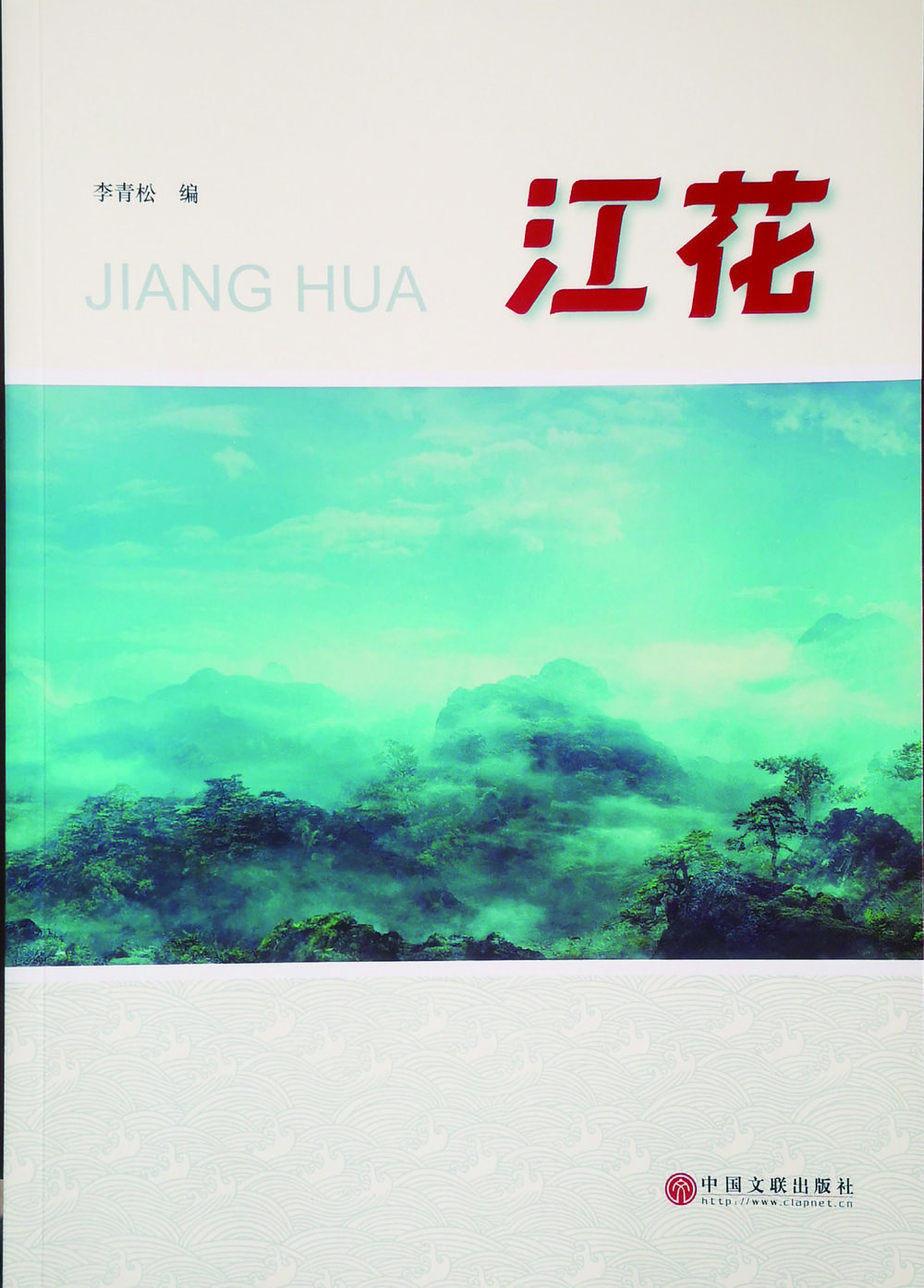在我的家乡,有一条发源自广西的河流。它一路奔腾,一路欢歌,溅起了无数浪花,也滋养了沿岸的美好诗意。“清清夫夷水,蜿蜒流远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演绎着尘世的无常……传递着众生的祈愿……九曲河床呵起伏波浪,谁是照亮前程的灯塔呵?”诗人李青松在歌曲《清清夫夷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其实,只要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青松以他的艺术涵养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和诠释。
十一年前,除夕的前夜,我自粤回邵与从京返邵的李青松在塘渡口古镇相遇相识。那天,我们与家乡的文人们欢聚一堂,谈诗论道,言笑晏晏。席后,李青松和我漫步在夫夷河畔的夜色中,我一边听他讲述邵阳县的文化历史,一边欣赏沿岸的美好景致。在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致中,在沿岸灯火的辉光里,我发现幽静的夫夷江面上,因为鱼儿的偶尔跳跃而溅起的“江花”闪烁着迷离的星辉,让我心生欢喜。而彼时,我并不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疾风中走过来的一批生活在夫夷河岸的心怀理想主义的有识之士,开始筹划创办了邵阳县新时期以来的第一个群众文艺园地,就命名为《江花》。
2015年秋冬时节,我在通读由诗人李青松主持编选的邵阳县千年文存《夫夷文澜》后,发现在邵阳县千年文化血脉中,除明清车氏诗文兴起的热潮外,新时期以来,夫夷水流淌的这片红丘陵上就曾涌起了三次巨大的文艺浪潮。
如果说天堂是博尔赫斯想象的图书馆的模样,那么,诞生在夫夷河流域的《江花》,就是培育本土文艺人才的“后花园”。在刘剑、邓杰等老师的辛勤耕耘下,《江花》杂志扶植推出了大批文艺新人。其中有很多优秀作品频频见诸于国家级报刊杂志,并时有作品在全国性征文比赛中获奖。如我所熟知的文学评论家张建安教授,他不仅擅写学术论文,还是一个高产的散文大家。2003年,张建安凭散文《那年那月》获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征文一等奖;2007年凭散文《物语夫夷江》获湖南省作协会“崀山征文”一等奖;2016年12月,张建安又凭借他的文学理论专著《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获得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江花》于1987年停刊了。虽然这本开创了邵阳县新时期文艺新风的阵地荒芜了三十余年,但在这期间,邵阳县青年追求诗和远方的理想主义情怀并未就此沉寂,继而出现了《哲理诗刊》《扬帆文学》《资江源》《邵阳诗人》《红丘陵》等文艺阵地,并涌现出了众多新时代的诗意抒写者和网络作家,其中以网络小说《遍地狼烟》入围茅盾文学奖的李晓敏影响力最大。从近年来这些文艺抒写者的创作实绩来看,邵阳县文艺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水平线越来越高,呈现出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时过三十余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经邵阳县宣传和文化部门一致研究决定,以图书的形式正式复刊《江花》,可喜可贺。我在读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复刊号《江花》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一是因为在异乡“重逢”家乡的刊物而喜悦,二是因为读了众多文艺工作者这么多高质量的作品而心喜,三是为组织编辑人员的辛勤耕耘而感动。认识诗人李青松十多年了,我们虽然相距千里,但时常互致问候,探讨诗禅美学。青松之于我,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在我困顿迷茫时,他常引领我参悟修行,提升心性,对我个人的成长,多有裨益。李青松少负诗名,曾北上任《青年文学》诗歌主持,创办《新诗界》,举办“新诗界国际诗歌大赛”,为新诗事业贡献了诸多心力。
收到青松寄来的复刊号《江花》是去年9月初,因为工作原因读完整本杂志,是最近几天的事。读完《江花》杂志上发表的优秀作品,再看这些作家的简介,我感觉诞生在夫夷水流域上的这些诗人学者个个都是了不起的,真是“夫夷‘江花’红胜火”啊。
读完《江花》,掩卷而思,我感觉编者把文艺理想融入了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通过刊发讴歌家乡人文、陶冶大众情操、升华灵魂境界、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使这朵火红的“江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从而为助推夫夷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心力,可谓功德无量。
(艾华林,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