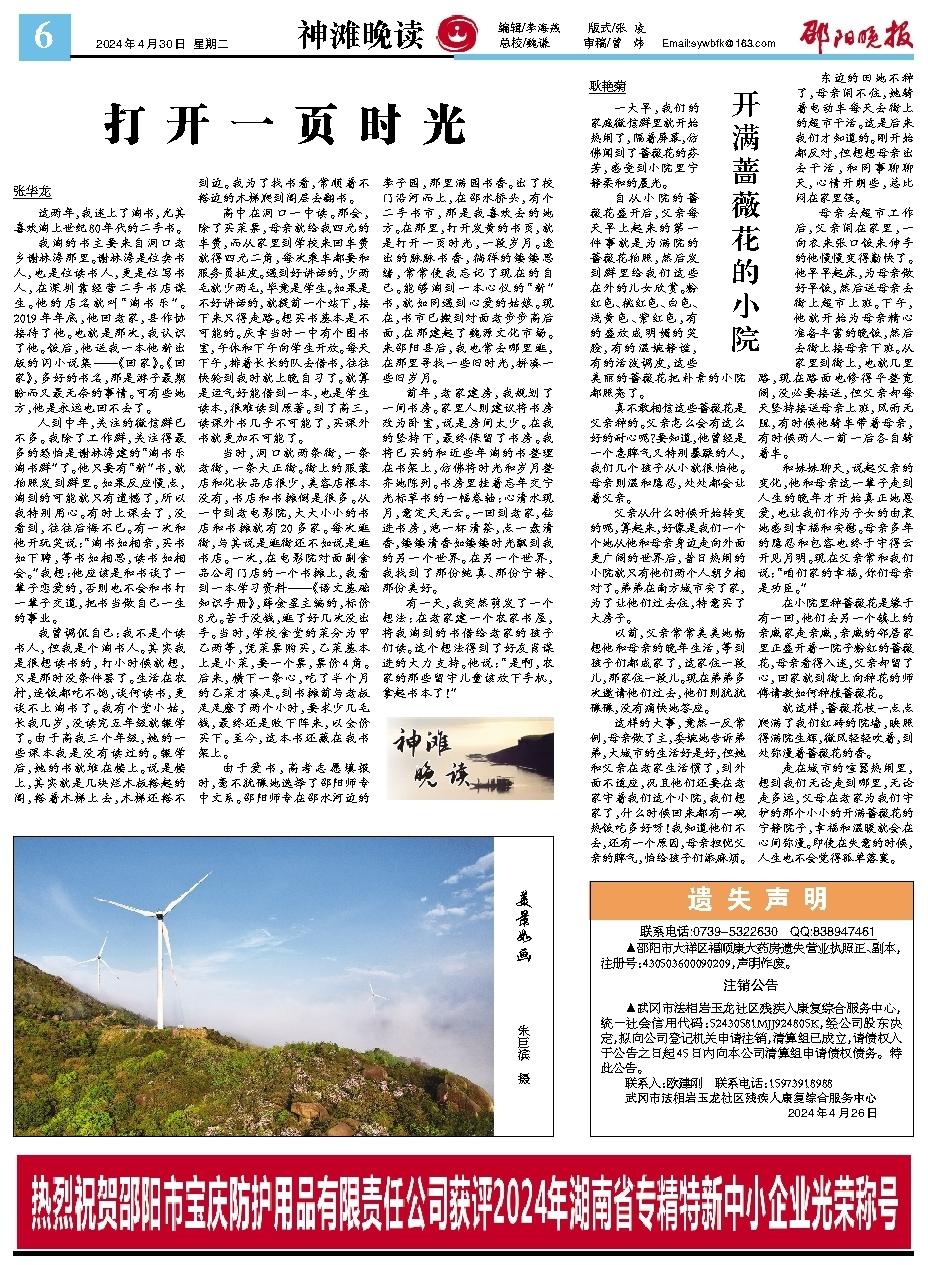这两年,我迷上了淘书,尤其喜欢淘上世纪80年代的二手书。
我淘的书主要来自洞口老乡谢林涛那里。谢林涛是位卖书人,也是位读书人,更是位写书人,在深圳靠经营二手书店谋生。他的店名就叫“淘书乐”。2019年年底,他回老家,县作协接待了他。也就是那次,我认识了他。饭后,他送我一本他新出版的闪小说集——《回家》。《回家》,多好的书名,那是游子最期盼而又最无奈的事情。可有些地方,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
人到中年,关注的微信群已不多。我除了工作群,关注得最多的恐怕是谢林涛建的“淘书乐淘书群”了。他只要有“新”书,就拍照发到群里。如果反应慢点,淘到的可能就只有遗憾了,所以我特别用心。有时上课去了,没看到,往往后悔不已。有一次和他开玩笑说:“淘书如相亲,买书如下聘,等书如相思,读书如相会。”我想:他应该是和书谈了一辈子恋爱的,否则也不会和书打一辈子交道,把书当做自己一生的事业。
我曾调侃自己:我不是个读书人,但我是个淘书人。其实我是很想读书的,打小时候就想,只是那时没条件罢了。生活在农村,连饭都吃不饱,谈何读书,更谈不上淘书了。我有个堂小姑,长我几岁,没读完五年级就辍学了。由于高我三个年级,她的一些课本我是没有读过的。辍学后,她的书就堆在楼上。说是楼上,其实就是几块烂木板搭起的阁,搭着木梯上去,木梯还搭不到边。我为了找书看,常顺着不搭边的木梯爬到阁层去翻书。
高中在洞口一中读。那会,除了买菜票,母亲就给我四元的车费,而从家里到学校来回车费就得四元二角,每次乘车都要和服务员扯皮。遇到好讲话的,少两毛就少两毛,毕竟是学生。如果是不好讲话的,就提前一个站下,接下来只得走路。想买书基本是不可能的。庆幸当时一中有个图书室,午休和下午向学生开放。每天下午,排着长长的队去借书,往往快轮到我时就上晚自习了。就算是运气好能借到一本,也是学生读本,很难读到原著。到了高三,读课外书几乎不可能了,买课外书就更加不可能了。
当时,洞口就两条街,一条老街,一条大正街。街上的服装店和化妆品店很少,美容店根本没有,书店和书摊倒是很多。从一中到老电影院,大大小小的书店和书摊就有20多家。每次逛街,与其说是逛街还不如说是逛书店。一次,在电影院对面副食品公司门店的一个书摊上,我看到一本学习资料——《语文基础知识手册》,薛金星主编的,标价8元。苦于没钱,逛了好几次没出手。当时,学校食堂的菜分为甲乙两等,凭菜票购买,乙菜基本上是小菜,要一个票,票价4角。后来,横下一条心,吃了半个月的乙菜才凑足。到书摊前与老板足足磨了两个小时,要求少几毛钱,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以全价买下。至今,这本书还藏在我书架上。
由于爱书,高考志愿填报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邵阳师专中文系。邵阳师专在邵水河边的李子园,那里满园书香。出了校门沿河而上,在邵水桥头,有个二手书市,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打开发黄的书页,就是打开一页时光,一段岁月。透出的脉脉书香,徜徉的缕缕思绪,常常使我忘记了现在的自己。能够淘到一本心仪的“新”书,就如同遇到心爱的姑娘。现在,书市已搬到对面老步步高后面,在那建起了魏源文化市场。来邵阳县后,我也常去哪里逛,在那里寻找一些旧时光,拼凑一些旧岁月。
前年,老家建房,我规划了一间书房。家里人则建议将书房改为卧室,说是房间太少。在我的坚持下,最终保留了书房。我将已买的和近些年淘的书整理在书架上,仿佛将时光和岁月整齐地陈列。书房里挂着忘年交宁光标草书的一幅卷轴: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一回到老家,钻进书房,泡一杯清茶,点一盘清香,缕缕清香如缕缕时光飘到我的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我找到了那份纯真、那份宁静、那份美好。
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在老家建一个农家书屋,将我淘到的书借给老家的孩子们读。这个想法得到了好友肖谋进的大力支持。他说:“是啊,农家的那些留守儿童该放下手机,拿起书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