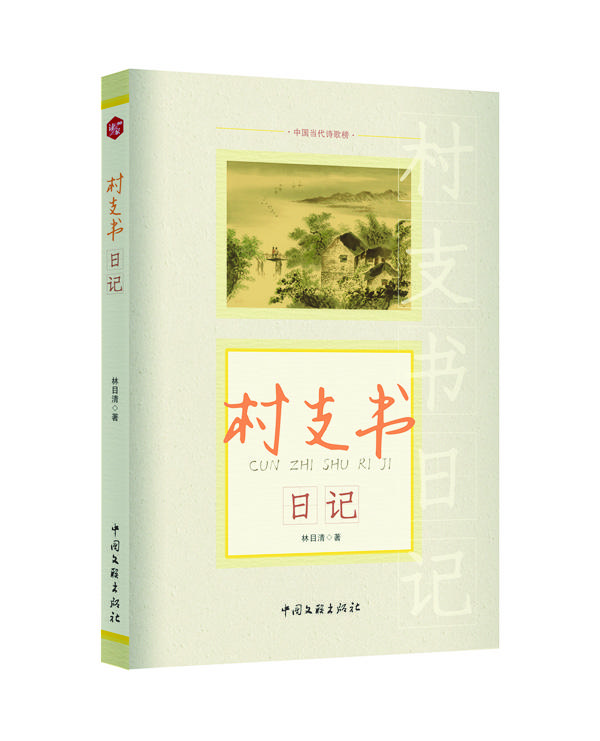林目清是一个有毅力的诗人,他有一种韧性,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坚持着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已在各类刊物中散播了40年,这让我看到了他对写作的执着和坚定,犹如水滴石穿,岁月虽长,他的笔端却从未停息。他已出版的诗集数量达到了十余部,部分诗集的销量甚至接近万册,足见他的作品对读者有一定的亲和感和影响力。
在读这部讲述乡村扶贫的诗集时,我深陷其中生动而真实的叙述。我曾在思考中慨叹,若作者能在扶贫的最后一刻出版这部作品,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目光,引起更多的讨论。然而,逆思而行,“文章千古事”,有时延缓的出版,或许是作者对作品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打磨,会赋予它更持久的光芒。将来沉淀在岁月的河床上,那些文字也许会因为时间的洗礼而更为夺目。
我想象未来的人们,在读到这部村支书的日记时,会沉浸在历史与文化的交融中,并深入挖掘日记与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读《村支书日记》中的诗作,窥一斑而见全豹。先分析讨论其中的日记之五十九,以及日记之一百五十三、日记之一百八十四。
这三首诗描绘了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沧桑历程,以及驻守的村支书的生动实践。我们从中可以触摸到中国扶贫工程的骨骼和脉络。
在“村支书日记之五十九”中,作者以诗的语言绘制了扶贫中的人口易地搬迁画卷。我们仿佛看见了一幅幅高山贫困村民迁徙至山下小镇的生动画面。这样的策略在许多地方得以实施,显现出中国精准扶贫的系统性思维。而诗人通过对贫穷的山地与相对富饶的山下小镇的对比描绘,剖析了社会结构的层级差异。
“村支书日记之一百五十三”中,诗人描绘出村支书内心的欣喜之情,他看见了农村社会生活从贫困向小康的微妙转变。诗人也点明了贫富之间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贫困的现象,也并非无法改变。
“村支书日记之一百八十四”更是巧妙地引导读者透过现象学的视角,走进村支书的生活现场。诗人细腻地勾勒出村庄改造的场景,如清理河道、改造厕所等,这也透露出了村民生活品质的日渐提升。通过这种直观的感官体验,读者能更深入“看见”扶贫的具体实践。
从审美角度来看,这三首诗注重了意象的经营。例如“精准地把一个小村庄连根拔起,移栽到山下的小镇上”“把名单移到了奔小康的页面”“我们村可以把溪沟整成标准化的水渠”。这些鲜活的画面增强了诗的感染力。在“村支书日记之五十九”中,诗人通过比如“蚂蚁族群还没反应过来”“这里的许多动物,从此没有人的相依陪伴”,揭示了贫困与自然生态的深刻关联,以及人类社会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不仅对当下生态环境的关注提出了犀利的呼应,也揭示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多元视角和复杂性。
在“村支书日记之一百五十三”中,诗人细腻描绘的生活细节,凸显了扶贫对普通人生活的改变。“手电筒、煤油灯、水车、风车……都收进了村级活动中心的博物馆了”这一句诗,透露出科技进步对农村生活品相的改变。而“村支书日记之一百八十四”则从乡村的基础设施改造入手,引发了关于乡村振兴和农民福利的思考。诗人通过如“屋檐水滴不出浊气”“阴沟里没有蚊虫横行”的描绘,传达出扶贫对于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村支书日记之一百八十七”中,诗人使用了许多具体的符号,如“喜鹊叫”“月亮睡到树梢上”“星星打瞌睡的眼”等,它们在诗歌的结构中相互关联,这种对符号和意义的处理呼应值得肯定。
总的来说,这些诗歌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是文化的见证,同时也是诗人对人性和社会的独特理解和批判。这些诗歌以其艺术形式,反映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实践。
然而,也需要注意到,像日记这样的第一手材料也有其局限性。作者可能会有主观性的偏见,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遗漏或者夸大某些事情。必须结合其他材料和研究,更深入的阅读将揭示出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中国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复兴。希望通过诗歌,呈现出一个和谐、多元、可持续的乡村形象,提醒我们关注并珍视这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不仅仅是美学的,也是社会学的,通过阅读思考,它启发了我们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思考乡村振兴的新视角。